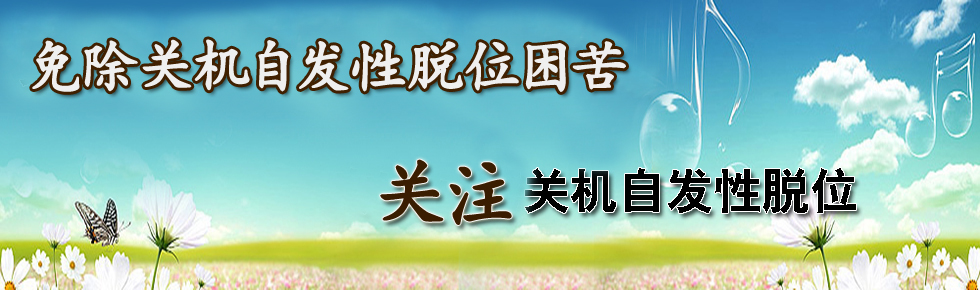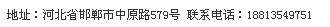神经外科医生做脊柱七致我敬重的北
一、讲故事
说起知晓王超教授,还有一个故事。
大约在10年前,我们开始做颅底凹陷的手术。那时我们还是经口腔做齿状突切除的年代,切完了由兄弟科室来帮我们做枕颈固定。后来我的师兄张晓彪主任带领我们做经鼻的内镜手术,我对这个区域开始感兴趣,查阅了大量的英文文献,并经常和骨科兄弟们讨论。一次,一位骨科的兄弟提及说王超教授是此领域的大牛。“王超是谁?”我随口说了句,结果遭到满场异样的眼光。我感受到那眼光背后的含义--“汝乃江湖宵小,老大都没搞清楚,安能行走江湖?”。哈哈,开个玩笑,原谅我是神经外科医生出身。不过,我回去翻了翻我那打印出来的厚厚一摞文献,果然找到了王教授的文章,而且上面有三色笔的圈画。从此,我养成一个习惯,注意看文章内容的同时,还注意一下出处。 Spine上王超教授的文章是年(王教授有很多文章,我指的是那个时候我学习的)。那时,我们上医对SCI文章还不作特别的要求,不像现在,没有SCI,不要说升职称,连报名也不好意思报。年,我也是第一次发SCI论文,不过是发在《Brainresearch》上的,激动了好久,医院大概就20几篇SCI论文(我们有强大的心、肝、肺研究所),可见那时候大家憋着劲发SCI的意识还不强,如果发了,一般还真是有点东西想讲一讲。年,王教授在Neurosurgery上发表了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令我印象深刻。由于地处上海,又是跨科,平时没有交集,但心里一直在想:王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王超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始,潜心研究治疗上颈椎疾病。95年,我才刚刚走出校门,所以王教授是前辈。王教授只做上颈椎,在国内这也是独树一帜。经他治疗的寰枢椎病例达例,他提出并改良了术式,设计并发明了器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脊柱脊髓大会在北医三院召开,虽然王超教授是骨科教授,但由于北医三院是主办单位。王教授也亲临参与互动。医院菅凤增主任(也是我的领路人)的大力推广,神经外科医生做颅颈交界的多起来。所提的问题也颇为犀利。但王教授神情清傲,不苟言笑,话语不多,回答干脆、自信,令人印象深刻。晚上晚宴,我坐在菅主任旁边。菅主任和王教授有过亲切的交流。大教授们宽容对待学术观点分歧的人生态度令我辈感触良多。这是我第一次当面接触到王教授。
再后来,我写了神经外科医生做脊柱(二),谈了我的成长历程、医院颅颈交界区诊治的发展。这篇文章的各种版本总的阅读量颇大。王超教授在专业
我特地把这三个位置的片子拿出来,放在一起。我们在改俯卧位时要注意O-C2角度,不能小于术前中立位。第三张是术后复查的最终角度,很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吃过2次亏。我曾经在全国会议上专门讲述过。
术后第三天,病人复查了颈椎磁共振和CT重建。可以看到齿状突切除范围满意,立体的图像比单独的矢状位更能显示全貌;这个病人,寰椎前弓皮质的连续性得以保留。在磁共振上,脑干的角度得以恢复。其实,这样的病人,-4天就可以出院。但由于患者说路途遥远,不放心,要多住几天,我也能理解,最后是6天出院的。出院的时候,高高兴兴地。 病例2:第二个病人是这样的;男,24岁,贵州人氏;他有一大堆片子。我所看到的他的首次影像医院东院拍的,可以看到他的斜坡基本平前颅底,有小脑扁桃体下疝。华山的一位医生推荐至天坛做的手术(患者的病历上都有记录)。手术做的是单纯后颅窝减压,切除了枕骨和寰椎的后弓,单单从术后的磁共振影像上看,后方得以减压,但患者的术前症状未能改善,医院求医。经王超教授推荐,来我门诊。我还没有收治入院,门诊匆忙,片子一大堆,留的资料不是很完整,给大家呈现的只是个大概印象。这个病人该怎么处理,我想不同的医生会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做前路?融合是个问题。如果以后做了,再向大家汇报。医院,实际上也是后路固定复位融合做的多(因为适合类型的病人多)。但是,由于国内做经鼻内镜前路手术的单位不多,医院在这方面做的早,比较成熟。所以这一武器我们一直在运用。(早期为了发展这一技术本身,不作选择,做的多一些。现在我们的基本选择标准和王超教授的推荐相似)。应该说我的师兄张晓彪教授带领我们开拓的这一术式已经在中山生根发芽,现在,连更年轻的医生都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且我们也知道肩上的责任,我们的坚持对丰富国内治疗这一区域疾病的治疗手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我们所信奉的技术以及我们自身,在潮流的更替和时间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之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