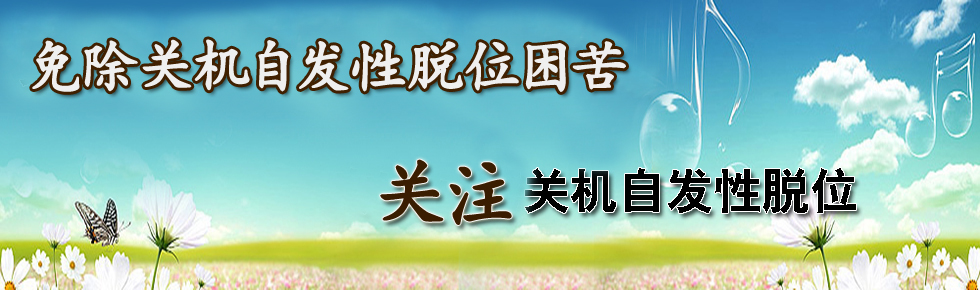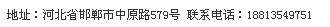萧红,错位的出走
因为《黄金时代》的缘故,十一前后零散的竟有半数时间在看萧红以及萧红相关的文字。无意中,竟然看到萧红是明末大家张岱的后人。便恍然,萧红那越轨的笔致与人生,至此便有了出处。
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其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那篇《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
有此一笔,若是女儿身,自当是柳如是、董小宛之流;更若有幸生于盛世,定是鱼玄机之辈。即便是未有善终,好歹也不枉担了“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虚名。这句口号式的电影宣传语,放在萧红身上,其实是奢侈的。
偏偏,张岱一身之文气与狂狷在多年后如此显性的遗传到了一个张家女儿身上;偏偏,此时的张家,家道亦是中落。一个偏远县城里落败地主家庭的女儿,最不需要的就是汪洋肆意的灵性与执着于内心的任性。于是,萧红有了第一次的出走,这也是萧红错位的原罪。
萧红是有相当的自觉地,她说:“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要说萧红的绯闻,今天看起来都说这女人脑子不太好使。然而,两度怀着前任的孩子与现任谈恋爱的故事,以及让无数后人腹诽意淫的与鲁迅之间若有似无的关系,都让“脑子不太好使”的断言总带着那么点“羡慕嫉妒恨”的意思。当然了,换了个脑子好使的林徽因,又要感叹客厅的女主人脑子太好使了。论起民国的女人们,若没有三两段绯闻加持,实在是没有什么有底气的,也撑不出女神的范儿。可到了萧红那,感情的事就是生活作风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
从陆振舜到汪恩甲,从萧军到端木,萧红每次出走都是追求自由或者爱情,但她每次都天真的将救命的希望放到一个男人身上。甚至是后来的骆宾基,是不是萧红心里的下一个希望,旁人不得而知。仅从当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萧红爱情命定的主题就是追求自由的新女性意识与男性依附的旧式思维。她关于爱情的错位出走,无异于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然而,还原到萧红当年的情景之中,站在萧红的角度,谁又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萧红,毕竟不是林徽因,出身名门,受过完整的西式教育及拥有更为宽容的生活环境;她也不是蒋碧薇,好歹徐悲鸿还带着去法国游历了一圈。从那个僻远的东北县城开始,出生的错位使她的天赋成为负累,而其女性资本所能触及的,她的选择也是有限。
汪恩甲是萧红最为人诟病的男人,后人纷纷揣测或者非议她和他之间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易,或者爱情究竟占比多少。可如果萧红是一个男人,那么这些声音就统统不会存在了。试想,一个进步少年遇到一个女子,依靠她的帮助摆脱了落后家庭的阻力,从此踏上自由光明的大道。这不生生就是一个革命青年的传奇励志故事么?即使再不济,他被女子抛弃,从此寄身花花公子之列,游走于各个女人间,也总有人会为他开脱,这是受过伤的男人,在背地里还不知道会被多少人艳羡。只能说萧红命真的不太好,她确实走上了自由革命的道路,也确实又和几个男人好过,但是那又如何?
坦白的讲,萧红的这种错位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即使在今天也有相当的讨论空间。邓文迪们的励志故事是不是这一主题的当代升级进化版呢?这样的主题,又是不是一个刻意针对女性的命题陷阱呢?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只是,唯有萧红把这种错位演绎得撕心裂肺,这是萧红的“本事”,也是萧红的“传奇”。也许,只有萧红自己明白这样的“传奇”背后的代价,所以在很多时候她保持着倔强的沉默。
不禁再去看看那个曾经站在萧红身旁的男人——萧军。真心不公平!都说萧军坦荡、磊落、真实,可是这个男人在今天看来绝对可以算作“渣男”。他是真的花心,不管是在萧红还是在王德芬身边,一直没有停止过出轨,甚至还搞上了自家女人的闺蜜。即使后来50年代初被打压的时候,一大把年纪了的他都不忘去招惹房东的小女儿,还生了个私生女。可是,他还是坦荡的,受人尊敬的。萧红的朋友们都不满意端木,认为萧红还是应当和萧军在一起。《黄金时代》里给萧军的海报里写着“想爱谁,就爱谁”,似乎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萧军的花心都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人们从来不忘在描述萧军的情史时,要加上“文武双全”四个字做背书。因此,萧军的花心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正常的。这是实在让人不明白的事情,民国时代女人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近来,关于民国大先生们寻欢烟花柳巷的段子,时不时的就会冒出一两段。但那是风月,赏玩一番大先生们的风流倜傥后,还是要用萧红的几段绯闻来苛责这个女人的。
当然,爱情可以被判无罪,花心可以归咎于本能。但是,至少能不能公平一些?可怕的是,这错位的偏见,至今还在。
是那个动荡的年代成就了萧红。一如萧红所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也如萧红所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中过的。”
萧红以诗文打动萧军,但其文学价值却始终未被萧军承认。即使在萧红死后,萧军也自负地认为萧红首先是“师我者”,然后才是“知我者”。这固然是萧军的大男人心态作祟,但又未尝不是那一圈左翼文人的价值评判标准的结果。
不得不说,是二萧的相遇,带来了萧红的黄金时代;却也是二萧的相遇,给萧红的黄金时代套上了牢笼。他开启了她的写作之路,却也强迫着她去接受他“政治优先”的价值标准。萧红是被动走进“左翼”作家圈子的,虽然有一干欣赏她才华的朋友,却不一定能够肯定她的价值。最为欣赏与怜惜她的鲁迅,也早早离世。对于萧红而言,又是一种错位的处境。
此时,萧红祖先身上的文心与倔强的基因再次被充分展现,她顽固的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二萧的分手,除了二人的性格不合及萧军的花心、家暴之外,创作理念上的歧见一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萧红再次出走,离开重庆到香港,朋友们多数是惊讶的,甚而是不谅解的。然而,不去延安,远离那个东北作家群却是必须的,因为她“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她没有张爱玲幸运,有一个相对宽松纯粹的环境单纯的写作,因为萧军的关系,因为从东北出来,因为鲁迅的赏识,因为周围的朋友,她的写作一开始就和政治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说,这次出走对萧红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幸运的是,只有在香港,萧红才能写出《呼兰河传》;不幸的是,即使在香港,她还是没有逃开战火的蔓延,最终客死异乡。
家庭、爱情、创作,每一个重要的关节,萧红都尴尬地处在一个错位的境地。她不甘,她出走,她沉默。萧红自述:“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但即使同时代的女人对她的苦楚也未必能够理解。四十多年后,梅志在《爱的悲剧》里的回忆,依旧弥漫出清楚的酸味。而许广平的追忆中渗透着深深的怨念也清晰可辨。丁玲当年的祭文看起来更像是一浇自己心中块垒。于是那些字里行间的所谓同情之意,相比之下不过是流于应景而已。
诚然,用今天的话来说萧红是不做死就不会死。她的天真、她的任性,她的自我沉溺都是她悲剧的原因。然而,萧红式的悲剧,在女性视角的命题上,今天也不一定能给出一个绝对完美的解决,更遑论一个非错即对的二元判断。
因为《黄金时代》掀起来一股萧红热潮,对于萧红,从不知到不解,从好奇到反思。萧红的话题性渐渐淡去,女性角度的思考重新开始。这也是《黄金时代》的另一种价值。
花边粉丝:兮然
/10/28
本文系文艺连萌成员花边阅读原创。欢迎分享,转载请事先联系,否则将追究责任。
支付宝打赏投稿邮箱:huabianyuedu
qq.白癜风治疗目标看白癜风要多少钱